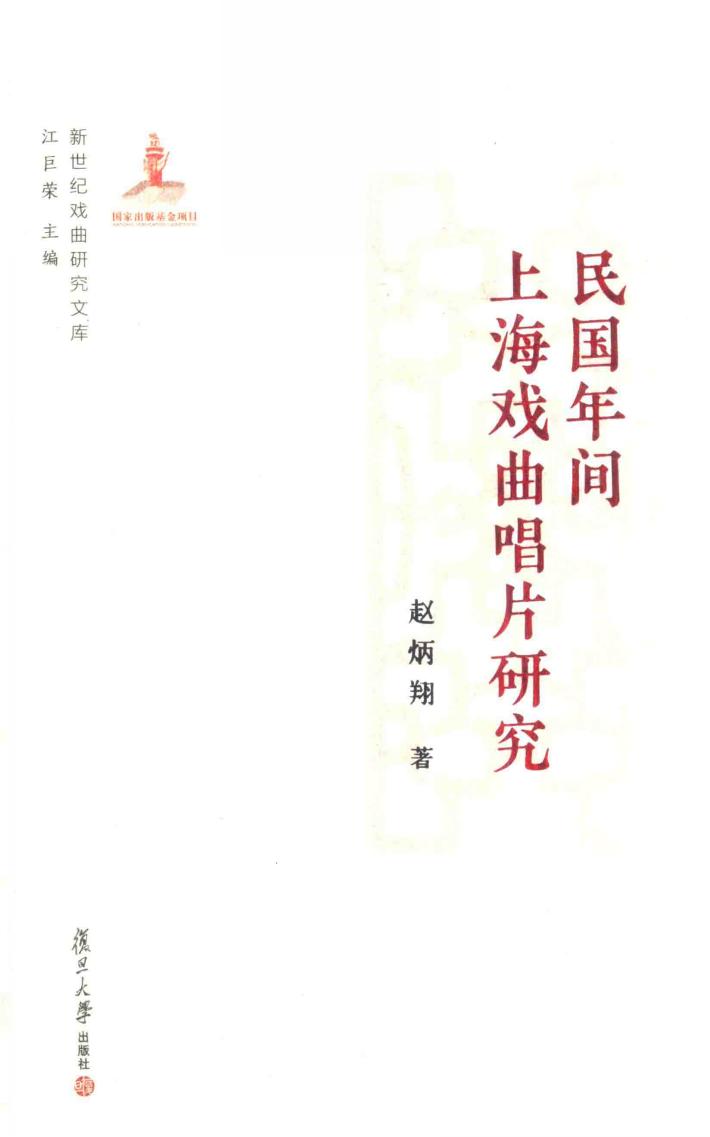
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
丛书: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
作者: 赵炳翔著
ISBN:978-7-309-13150-5
关键词: 戏剧史-研究-上海-民国
页数:396
出版社: 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
出版日期:
发现《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》在 2025-09-22 可全文阅读或下载。
图书简介
序赵山林19、20世纪之交,京剧和秦腔、梆子、粤剧等地方戏曲蓬勃发展,争奇斗艳,昆曲则以各种方式勉力传承,以图留雅音于一脉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的戏曲市场总体繁荣,各阶层的观众队伍日渐壮大。与此同时,作为当时西方新技术成果的留声机、唱片传入中国,某些商家敏锐地抓住了初步显露的商机,促使艺术与技术、艺术与商业不失时机地相互结合,戏曲唱片这一新鲜事物的应运而生。从此,源远流长、丰富多彩而又依赖口耳相传、难以原声原貌传之久远的中国戏曲,有了一种新的保存和传播途径。随着众多戏曲艺术名家的倾心投入,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”不再成为戏曲爱好者的感叹,借助唱片,戏迷可以循环往复、从容不迫地欣赏戏曲那种“感心动耳,荡气回肠”(曹丕《大墙上蒿行》)的美妙音乐,“闻其声如见其人”成为许多戏迷的艺术享受。可以说,唱片的出现,对于戏曲受众面的扩大和进一步普及,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和艺术水平的提升,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。关于戏曲唱片在上海的流行,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颐安主人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中有《留声机器行》二写道:伶人歌唱可留声,转动机关万籁生。社会宴宾堪代戏,笙箫锣鼓一齐鸣。买得传声器具来,良宵无事快争开。邀朋共听笙歌奏,一曲终时换一回。顾炳权编著《上海洋场竹枝词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6,第133页。可见距今110年前,圆盘唱机和戏曲唱片已经在上海流行开来。戏曲唱片的流行,甚至影响了戏曲艺人与票友的心态。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1902年10月21日记云:“自西人留声机器输入,于是凡精此技者皆大喜,以为吾辈所长,亦可不朽。”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,第582—583页。传统的观念,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三不朽,此处以留声留艺为不朽,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态变化。正因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,戏曲唱片逐渐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。除国家重点支持的老唱片拯救工程之外,有关研究成果也逐渐涌现,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,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。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戏曲唱片,相对于唱片与戏曲关系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,这一研究的拓展空间还是巨大的,而针对某一时段、某一地区的戏曲唱片的整体研究成果甚少,也使我们觉得有研究进一步开拓的必要。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,赵炳翔君本书选题有其的价值。说本书选题有其的价值,是因为上海与戏曲唱片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。上海是中国唱片的发祥地,绝大多数戏曲唱片都是在上海生产与发行的,而且代表了戏曲唱片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。赵炳翔君生于上海、长于上海,长期从事音乐、戏剧研究工作,对于音乐、戏剧艺术既深爱之又深知之,从事这项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本书的成功,先在于构思和撰写过程中贯彻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,即以民国史、社会生活史、戏曲史、都市文化学为研究基础,综合运用戏剧戏曲学理论,从田野调查、文本分析与唱片实物考察三条路径的结合上进行研究。本书从宏观上对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发展脉络作了梳理。作者从留声机的传入与上海唱片业的形成、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灌制与生产概况,以及民国年间广
用户须知
出版社通过教客网下载电子书并起诉站长多次,本站随时可能倒闭。
诉讼案号:(2022)川01民初4401,(2022)川01民初4403,(2022)川01民初4403,(2022)川0191民初19351号, (2022)川0191民初19594号,(2022)川0191民初20457号,(2022)川0191民初20459号, (2023)川知民终373号,(2023)川知民终374号,(2023)川知民终375号, (2024)川0191民初15977号,(2024)川0191民初15979号,(2024)川0191民初15980号, (2024)川0191民初15981号,(2024)川0191民初15982号
- 找《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》,去就近图书馆。
- 本页面文字内容和图片来自 m.5read.com。
- 封皮图片引用地址:https://cover.duxiu.com/coverNew/CoverNew.dll?iid=62656066646860686264579fa090a892a596a39e92a39c3737333233363731
